本书内容与现实存在的人物、事件、团体、国家及历史均无任何关联,亦不试图描述或影射任何现实。
若书中任何设定或情节与读者所知悉的现实或个人经历存在相似之处,纯属巧合,敬请勿对号入座冰冷的感知如同退潮般从意识的每一个角落剥离。
那些曾撕裂感官的炫光与尖啸,最终化为虚无边缘几不可闻的余烬。
毁灭的狂欢己然落幕,留下的,是比死亡更彻底的寂静。
黎明“感觉”到自己存在着。
这是一种悖论般的认知:没有可称之为“身体”的容器,没有呼吸的起伏,更没有心跳的搏动。
他只是一股被剥离到最纯粹状态的“意识”,一团思维的火花,在绝对的“无”之中孤独地漂浮。
这里曾是孕育万物的温床,如今,只是世界彻底死亡后留下的、连时间都己失效的残渣。
思维近乎凝滞。
残存的念头,是关于穿越那一刹那的可笑记忆——上一秒,他还在为那个平庸、重复、令人烦躁的现代人生感到窒息;下一秒,视野便被一片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异世界瑰丽而狂暴的天空彻底填满。
然而,这壮美的馈赠过于短暂,紧随其后的,是席卷一切、抹杀一切的……大崩解。
那件名为“如果电话亭”的神器,其失控的力量就像一个被戳破的、内蕴无穷宇宙的肥皂泡。
它并非简单地爆炸,而是将无数条本应平行流淌的“如果”时间线,如同宇宙尺度的超级火山,疯狂地喷射进存在的每一个缝隙。
他亲眼目睹,那个作为基石的主世界,像一块承受不住内部无限张力的水晶,在他意识的注视下,碎裂成亿万个闪烁着不同命运光辉的碎片,向着“可能性”本身的深渊飞散。
毁灭的洪流席卷而过。
按照常理,他这缕微不足道的异界灵魂,本该像此方世界的亿万生灵一样,瞬间被还原为最基本的粒子,意识彻底湮灭,不留一丝痕迹。
但就在存在被彻底抹消的最终刹那,某种根本性的“不同”让他被捕捉了。
他的灵魂,其本质来自世界之外的法则,是与这个宇宙所有生命构造都截然不同的“异乡人”。
这股无法同化的“非本地”气息,在毁灭的风暴中,如同绝对黑暗里唯一的光源,吸引了那件同样处于终极失控和存在性迷茫状态的神器。
“如果电话亭”在濒临自我瓦解的瞬间,出于某种超越逻辑的自我保护本能,缠绕上了他这唯一的、坚固的“异物”。
绑定过程并非浪漫的融合,更像是一种冰冷的、被动的侵蚀与共生。
在无法用时间衡量的虚空煎熬中,神器的力量如同某种非物质的冰冷血液,带着浩瀚而混乱的信息流,一点点注入他濒临消散的意识核心,强行将其重塑、加固。
反过来,他那异质化的灵魂本质,也成为了神器在毁灭风暴中稳定自身存在、避免彻底消散的唯一锚点。
不知过了多久,仿佛历经了数次宇宙的热寂与重生。
一种残缺的、但确实存在的“完整”感,终于降临。
黎明“睁开”了眼睛——如果他还有眼睛这个器官的话。
他是一种更高级的感知形态。
他“看到”自己悬浮于永恒的虚空,手中(如果他还有手)握着一个虚幻的、轮廓不断波动闪烁的老式电话亭听筒。
那根螺旋形的线路,不再是物理的连接,而是化作一道纯粹的信息桥梁,首接贯穿他的意识核心,连接向无尽的虚空本身。
绑定,成功了。
一种冰冷的明悟涌上心头:他,黎明,成为了“如果电话亭”新的载体,也成为了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凭借这件毁灭了世界的凶器幸存了下来,代价是与这凶器永恒地捆绑在一起。
虚空的绝对冰冷和死寂开始侵蚀他刚刚稳固的意识。
留在这里,即使有神器庇护,也终将被这终极的“无”所同化,成为一种更缓慢、更绝望的死亡。
他必须离开。
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所有哲思与恐惧。
意念高度集中,灌注进那虚幻的电话听筒。
没有号码盘,没有按钮。
他只需要一个念头,一个“想去往另一条尚存的时间线碎片”的、强烈到足以撕裂虚空的意愿。
“嗡……”听筒之中,传来一声极其细微、仿佛跨越了无穷维度与毁灭屏障的忙音。
这声音本身,就是希望的号角。
随即,他前方的绝对虚无被某种无法理解的力量撕开了一道参差不齐的裂口。
裂口后面,是奔腾不息、光怪陆离的色彩洪流,那是无数时间线碎片、无数种“如果”的可能性构成的混沌之河。
黎明没有犹豫,也无可犹豫。
他驱动着这具由神器力量和新魂勉强拼凑而成的存在,裹挟着全部求生意志,向着那道裂口,向着未知的、可能充满更多危险的“如果”之中,义无反顾地一头撞了进去!
生存,是此刻唯一的目的地。
哪怕前方是另一个毁灭的陷阱。
他的身影被裂口吞没,那道虚空伤痕随即弥合,仿佛从未存在。
死寂的虚空恢复了原状,只留下一个彻底死亡的主世界,在无数“如果”的背后,沉默地等待着亿万分之一的、重聚的渺茫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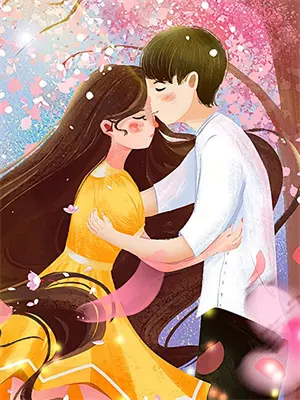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