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叫头遍时,我己经醒了。
窗外的天还泛着墨蓝,灶房里却己亮起微光。
娘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被油灯拉得老长,木柴在灶膛里噼啪作响,混着玉米糊糊的香气飘过来。
我披了件打满补丁的粗布褂子坐起身,炕梢的小妹还在打鼾,脸蛋红扑扑的,像个熟透的苹果。
"醒了就起来喝口热的。
"娘回头看了我一眼,手里的木勺在陶锅里搅了搅,"今日得早些去村头晒谷场,里正说官府的人要来讲事。
"我应了声,穿鞋时脚心踩着冰凉的泥地,忽然想起昨儿在后山菜窖里看到的景象——窖角那筐特意留着的晚熟红薯,表皮竟泛着不正常的青黑,像是被冻坏了。
今年的秋意来得格外早。
刚入九月,早晚的霜就厚得能压弯狗尾巴草,田埂上的野菜蔫头耷脑的,连最耐冻的冬麦都迟迟不肯冒芽。
村里的老人聚在老槐树下念叨,说这是天兆,怕是要有大事。
我舀了碗糊糊蹲在门槛上喝,玉米的清甜混着淡淡的苦涩滑进喉咙。
爹扛着锄头从院里进来,裤脚沾着晨露,他黝黑的脸上刻着深深的沟壑,见我望着西边的山头发愣,闷声问:"在想啥?
""想菜窖里的红薯。
"我扒拉着碗边的玉米粒,"是不是该提前挖出来晒晒太阳?
"爹没说话,只是往灶房里看了眼,娘正往布包里塞着蒸好的窝头,动作快得有些慌乱。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几日爹娘总在夜里压低声音说话,油灯要亮到后半夜,想来不是寻常事。
"吃完了跟我去晒谷场。
"爹放下锄头,接过娘递来的窝头,咬了一大口,"让你娘在家看妹妹。
"小妹被我们的动静吵醒,揉着眼睛要娘抱。
娘哄着她说去灶房拿糖块,转身时我瞥见她眼角的红痕。
晒谷场己经聚了不少人。
村口的老槐树底下,里正李伯正踮着脚往西边张望,他那件浆洗得发白的长衫被风灌得鼓鼓的,像只张开翅膀的灰鸽子。
男人们蹲在石碾子周围抽着旱烟,烟雾缭绕里满是压抑的咳嗽声;女人们抱着孩子聚在一旁,眼神里藏着不安,时不时瞟向通往镇上的那条土路。
"薇丫头,你爹呢?
"隔壁的张婶凑过来,她怀里的小儿子流着鼻涕,正揪着她的衣襟啃。
"去给地里的麦子盖草帘了。
"我往人群外挪了挪,避开那孩子蹭过来的脏手,"张婶,你知道官府的人要来干啥不?
"张婶的脸色僵了一下,压低声音说:"前儿去镇上赶集,听茶馆里的说......说北边打仗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
北方的战事断断续续闹了快十年,听说是朝廷跟那些骑着马的胡人打,打打停停的,离我们这江南水乡远得很。
村里的壮丁被征走了两批,回来的没几个,剩下的人日子照过,只是逢年过节烧纸时,会多往北边的方向磕个头。
"打仗......跟我们有啥关系?
""谁说得准呢。
"张婶叹了口气,摸着怀里孩子的头,"听说朝廷打赢了,占了好大一块地盘,就是没人住,要......要从南边迁人过去。
"迁人?
这两个字像块冰,顺着我的后脖颈滑下去,冻得我打了个哆嗦。
"嘀嘀——"一阵清脆的马蹄声从西边传来,人群瞬间安静下来。
三匹高头大马踏着晨雾奔来,为首的是个穿着青色官服的中年人,腰间挂着铜牌,在朝阳下闪着冷光。
他身后跟着两个挎着刀的兵卒,马鞍上的红缨随着马匹的跑动轻轻摇晃。
里正李伯赶紧迎上去,弓着腰作揖:"小人见过大人。
"那官差勒住马,居高临下地扫了眼黑压压的人群,声音像淬了冰:"奉朝廷令,即日起,江南各府凡家有壮丁、田产不足十亩者,皆需北迁,前往云漠、朔方二州定居。
""哗——"人群像炸开的锅。
"啥?
要迁去北边?
""那地方不是说全是沙子吗?
种得出庄稼?
""我不去!
我死也不离开祖宗坟地!
"哭喊声、咒骂声混在一起,几个年纪大的老人当场就瘫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嚎啕大哭。
我挤在人群里,看着那官差冷漠的脸,手脚冰凉——我们家的田,正好九亩半。
"肃静!
"官差拔出腰间的佩刀,刀身在阳光下晃出刺眼的光,"此乃皇命,抗旨者,斩!
"哭声戛然而止,只剩下风吹过晒谷场的呜咽声。
官差从马背上取下一卷黄绸布,展开来,上面盖着鲜红的大印。
他念着上面的字,声音平板得像庙里的木鱼:"......北地新收,亟需垦荒,凡迁徙者,每户分良田二十亩,免赋税三年,途中供给口粮......"后面的话我没听清。
二十亩良田,免三年赋税......这些话像钩子一样勾着人的耳朵,可谁都知道,那北边的土地埋了多少白骨。
前两年从北边逃回来的流民说过,那里的风能刮走人的皮,冬天能冻掉石头,胡人虽被打跑了,可零散的马匪比狼还凶。
"这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吗?
"不知是谁在人群里低吼了一声。
官差的眼睛立刻瞪过去,那目光像刀子似的:"朝廷赐地免税,是天大的恩典!
尔等刁民,竟敢妄议!
"他朝身后的兵卒使了个眼色,"把名册拿来。
"一个兵卒从包袱里掏出本厚厚的册子,官差接过,开始念名字。
"王老实家,三口人,田七亩,迁!
""李柱子家,五口人,田五亩,迁!
"每念到一个名字,那户人家就像被抽走了骨头,有人瘫倒,有人哭喊,还有人红着眼要冲上去,被兵卒用刀背狠狠打了回去。
"林大山家。
"听到爹的名字,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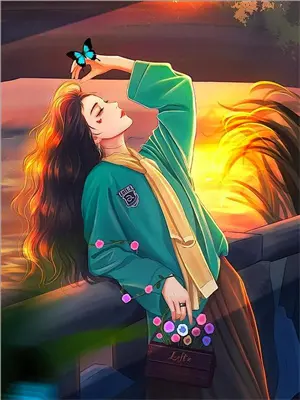
最新评论